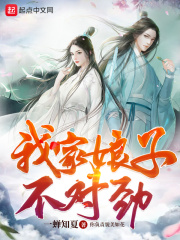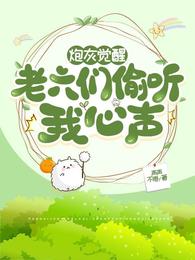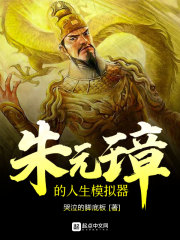52小说网>从小镇做题家苟成大医起点 > 第七百九十三章 胡青元的历练(第6页)
第七百九十三章 胡青元的历练(第6页)
他在很多课题里的参与份量不够高,只是挂名的话,也不能以CAA拿到特别好的科研奖励。
不然的话,挂名的含金量就过高了。
胡青元摇头回道:“师父,当然不会啦,如果我要发文章的话,我在恩市做出来的工作量都够发一篇七八分的论著了。”
“但课题没做完,只是发局部的话,意义就不算大了。”
“而骨肉瘤一条全新独属MiRNA的价值,含金量非常高的,有可能对骨肿瘤的诊断进行重新定义。”
“这个课题,值得好好做……”
胡青元先列举现实,而后才道:“师父,再说了,哪怕我真的啥也没做,你且当我做过了,给我点什么东西,又哪里是林方忠他们可以抗衡的?”
“我已经拥有了最好的资源,还是多给他们留点机会吧……”
胡青元此刻的心态有点类似于网络上很出名的‘不豁取’最底层资源理论。
家里宽裕的人,千万不要想着去压榨垃圾桶里那点微薄的残余资源,那是留给一些人最后的生存线。
于胡青元而言,他有钱,还可以分到不少的科研奖金,要做的课题也有,只是没有阶段性的成果作为激励,但前途无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青元只需要做好不羡慕,维护好自己的心态即可。
“我们可以这么想,但不能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思去这么做事,去做人。”
“现在的你,我之所以不再建议你去申请校级课题和市级课题,是因为我们课题组不需要这个经费支持。”
“但很多课题组还需要,很多其他人还需要。”
“你不需要一个校级和市级课题给自己增加履历的厚度,但肯定有其他人需要。”
方子业说到这,眯了眯眼睛:“那时候是真的需要啊,十万块钱对我们来讲……”
其实那个市级课题结题还没多久,方子业还对它记忆犹新。
它虽然只有十万块钱,但这十万块,对于当年的方子业而言,就真的是雪中送炭了。
胡青元知道,一些知名教授的课题经费,一般也就是几十万,多的可能有两三百万。
大部分小导师,能够支配的科研经费基本上也就是一二十万。
甚至有一些导师,他们申请的课题经费,都是为了购买下一个课题而用,自己再掏一部分钱去买数据,买文章,再买课题……
他们收进来的学生,不仅没有自由支配的课题经费,还要给课题组打工,这才是真正的“科研牛马”!
像自己老师这样,自己才是第一个学生,基本上就可以实现经费自由的,放眼全国都少之又少。
胡青元想了一会儿,说:“师父,其实我现在稍微有点点迷茫。”
“就是吧,如果我一直搞临床的话,我就必须得放弃科研,如果我一直带着科研的话,那么我就无法专注于临床,也不好尽早地给师父您帮忙!”
“科研肯定会拖累我的临床进展。”
“师父,您以前是怎么平衡这个时间的?”
“就纯熬嘛?”
方子业心道:纯熬了几年都没用,开了才有用,你师父方子业懂个屁的平衡?全靠了加点而已。
不过,胡青元的问题他还是要回答的:“师父当初是纯熬过来的,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人引路,就是靠着机械性地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