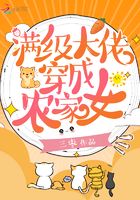52小说网>清穿从小佐领到摄政王txt > 第165章(第6页)
第165章(第6页)
德亨略迟疑问道。
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意思是,度量人们认识上的“过”与“不及”两个极端的偏向,用中庸之道去引导他们。
用在德亨身上,就是,德亨要先低下头,找到普通人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点就是正常普通人能接受的普众标准,站在这个普众标准上,他就能度量人心,平衡局势,进而运筹帷幄。
这就是儒家提倡的中庸。
陈廷敬垂首:“尽言矣。”
德亨太聪明了,只有已经站到顶端的很少一部分人才能跟得上他的思维,看的透他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
他站在金字塔顶端这个高度上去看别人,尽是“愚蠢的人类”……
他要是对蒙古少年们这样还好,或许迟钝的都没发现自己被鄙视了?
但当他对上康熙帝,开始有了“不过如此”“封建帝王”“没有跳出时代的局限性”这样的思想苗头的时候,离自取灭亡就不远了。
就拿这次他擅自在古北口停留一天这件事来说,他派芳冰来追上圣驾,是在通知康熙帝,我要在古北口一天,而不是请旨,问康熙帝,是否允许他在古北口停留一天。
德亨这种行为,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先斩后奏”。
芳冰回话的时候,陈廷敬就在伴驾,当时他真是替这位德公爷捏了把汗,康熙帝随口一句:“知道了”就过了,但谁知道,以后会如何呢?
帝王心思,你最好别猜,也别寄予厚望。
德亨:……
再说回课堂。
好吧,这个浸淫宫廷和官场一辈子的老狐,是在告诉德亨,在有皇子在的时候,就算你答的再好,先生也不会夸你的,因为在先生这里,你是“不可能”比皇子还要优秀的。
陈廷敬用实际行动和若有若无的点拨在教导德亨不要太露锋芒,该藏拙的时候要藏拙的道理。
其实这也是这一堂课的中心思想,中庸之道。
你优秀,你表现出来了,先生也知道了,就行了,就不要执着于这浅显的“名利”了。
陈廷敬作为一堂之师,该做的,该教的,都教了。
至于学生能学到多少,就看个人悟性了。
德亨喃喃:“要是我没找出来,跟你要个说法,误解了,你不怕我记恨你吗?”
陈廷敬:“您可有想过,您身边不如您的人,可会嫉恨您呢?”
德亨第一个想到了弘晖和德隆,脱口而出道:“当然不会……”
说完,又后知后觉的想到,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为什么就不会呢?
他们生来就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处处都低他一头。
再者,就算弘晖和德隆不会,难道胤礼和胤祄这些和他差不多年岁的小阿哥们不会吗?
他们是天潢贵胄,是皇子,你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宗室凭什么会抢了皇父本就不多的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