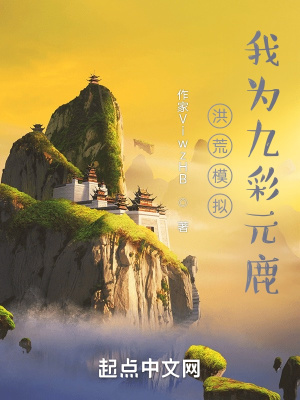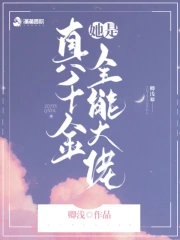52小说网>大秦歌谣 > 第415章 珠联璧合(第1页)
第415章 珠联璧合(第1页)
萧何抚摸着怀中那份小心包裹的的路引文书的轮廓,隔着布料,仿佛也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期许。
上面清晰地写着他的姓名“萧何”,籍贯“沛丰邑中阳里”,以及那句让他每每想起便热血沸腾的评语:“有志法家,可堪琢玉”。
这份文书,不仅是他叩开咸阳大门的凭证,更是那位近一年来,暗中对他关怀备至的恩人,对他的认可与期许。
萧何每每想起秦臻在下邳墨社高台上挥斥方遒的身影,想起他描绘的那个以法为纲、秩序井然、国力蒸蒸日上的秦国,再对照眼前这鲜活真实的景象,萧何胸中就激荡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
自卑仍在,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已拔节生长:他一定要在这片土地上,学有所成,立身行道,亲眼见证、甚至亲手参与那太平盛世的构建。
渭水在官道右侧奔流,水声浩荡,仿佛呼应着萧何胸腔内愈发汹涌的波涛。
他驻足片刻,目光越过粼粼波光,望向咸阳方向。
那里,秦国的心脏正在强劲搏动,而他,一个来自楚国乡野的平凡少年,竟真的踏上了这片土地,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文书,即将叩响那扇厚重的门扉。
“萧兄,望什么呢?莫非是近乡情怯?你这‘乡’,可还没到呢。”甘罗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和一丝促狭,,打断了萧何的沉思。
他身量尚显单薄,但那双眼睛却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锐利与灵动。
且甘罗面容清秀,举止间带着世家子弟特有的从容优雅,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气度是萧何暂时无法企及的。
萧何回过神来,露出一抹温和却带着深思的笑意,摇摇头:“非也。只是越近咸阳,何心中感慨愈盛。
昔日在下邳,于百家大会角落仰望秦先生风姿,听闻先生描绘秦国之志、法治之威,只觉振聋发聩,心向往之如渴。
如今亲身踏上秦地,眼见这官道平整宽阔如砥,往来商旅货物分明、井然有序;
驿站厩舍齐备,补给充足及时;
沿途里闾虽简朴,却少见流离饥馑之色。。。。。。
方知先生所言非虚,并非空中楼阁。
秦法之下,秩序井然,国力凝聚,确有其独到之道。”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许,带着几分沉重:
“反观我楚国腹地,权贵奢靡无度,赋税徭役盘剥如虎,百姓面有菜色,路有饿殍无人问。。。。。。这反差,直如天壤之别。
难怪秦国能如此吸引天下英才,此非幸致,乃循法务实之必然!”
甘罗闻言,收起几分戏谑,老气横秋地点点头,眼中闪烁着与年龄不符的精光:“萧兄洞察深刻。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以法为纲,耕战立国,励精图治数代,方有今日气象。
律法严明,赏罚必信,此乃强盛根基。
罗偶然间听闻,咸阳气象日新,贤才汇聚如百川归海,皆赖大王雄才伟略与秦先生运筹帷幄。
秦先生于百家大会上纵横捭阖,将法家治国之要剖析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