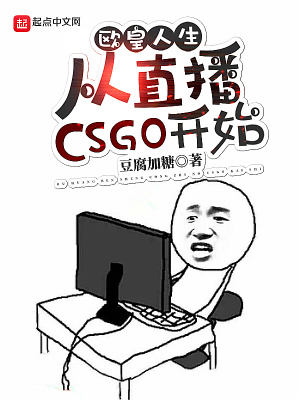52小说网>宝换个姿势再来 > 第1508章 养得出野草养不成大树(第3页)
第1508章 养得出野草养不成大树(第3页)
曾敏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什么波澜。
走到窗边,用指尖撩开那脏污布帘的一角,望了一眼楼下混乱嘈杂的麻园街景,扭曲的电线杆,蜘蛛网一样的电线,破烂坑洼的路面,奔跑的野狗,油腻的摊位,违章房的屋顶晾晒的花床单在热风里招摇。
这光怪陆离的艺术贫民窟,就是这两个年轻人挣扎着供养梦想的土壤。
转过身,走到小平头刚才未完成的仿作前,拿起笔,在脏兮兮的调色盘上勾勒几下,精准地点在芭蕾舞裙摆边缘一抹极淡的钴蓝冷光上,“这里,原作用的是群青加一点点玫瑰红调出的灰,冷中透暖,像早春湖面反光。你用酞青蓝加白,省事,但薄了,也死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说着,抹了几笔,又把笔递给吴川,“自己看看。”
吴川接过笔,看了眼画,一愣,眼中闪出恍然,郝大有也瞧向画。
曾敏把草帽在手里随意地转了个圈,看向两个年轻人脸上,那眼神不再是审视画作时的锐利,反而带上了点,近乎是长辈看自家不争气又倔强小辈的复杂意味。
“麻园这地方,养得出野草,养不成大树。”
“野路子画到死,也就是个画匠。想当画画的,根子得扎在土里,苗子得朝着光长。你们这点子野劲儿,野得不对地方。”
目光在长毛那布满血丝却依旧倔强的眼睛和小平头紧抿的嘴唇上停留片刻,像是在做最后的掂量。
然后,曾敏抛出了一句话,“滇艺、川艺考不上,换个地方考,去燕京,试试央美,怎么样?”
“……”
央美。
两人瞳孔骤然放大,像被强光照射到。
身上那混杂着疲惫、绝望和最后一点硬撑的倔强,被一种巨大的、不敢置信的茫然和恍惚所覆盖。
嘴唇微张着,像是两尊骤然僵化的泥塑。这两个字像一道凭空劈下的闪电,炸得他们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嗡嗡的回响。
央美?
那是云端上的名字,是无数个在麻园潮湿闷热的夜里,他们只敢在画布前偷偷咀嚼,随即又会被冰冷现实砸碎的幻影。
这念头本身就荒谬得像麻园违建房墙上最癫狂的涂鸦。
他们连滇艺那道该死的两百多分的文化门槛都迈不过去,央美,那是比滇艺更高、更险峻、更加不可及的绝壁。
还有去燕京?那地方对他们而言,是地图上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是晚上七点片头曲里恢弘的配乐,是所有传说里,生活成本高昂到足以压垮他们的庞然巨物。
吴川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脚跟撞到身后的画架腿,发出“哐当”一声轻响,那幅接近完成的芭蕾少女仿作在架子上轻轻晃了晃。
他看着曾敏,眼神里充满了惊惧和本能的退缩。
郝大有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胸膛剧烈起伏,试图从曾敏那张平静得的脸上找出一点玩笑或者嘲弄的痕迹。
没有。只有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沉甸甸的东西。
人,就像是站在悬崖边,被人猛地往前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