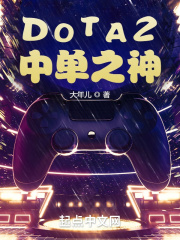52小说网>家祖左宗棠在线阅读全文无弹窗 > 第501章 苦战(第2页)
第501章 苦战(第2页)
号航空母舰每天放飞飞机,用这种防空火力薄弱的阵地练手,至少起降飞机已经练的挺熟练的了。
“鹰”号在被俘虏之后并没有改名,而是依照惯例沿用旧名,可以想象,“鹰”这个舰名之于中国,就好比“企业”之于美国,“可畏”之于英国,是日不落帝国落日的象征,必然是经典永流传。
这艘航母的底子是一艘早期战列舰,战舰完工度又高,改造潜力很低,换装国防军的飞机之后,载机量只有20架,只能做点支援护航工作。
相比之下,作为进攻学派理论主导的战舰,“太岁”号以1。7万吨的排水量实现了72架常用、8架备用的最大载机量,代价自然是鱼雷防护的薄弱和稳定性的下降。
(这两艘航母停在莫尔兹比港外,颇有一种鹰和胡蜂在地中海的感觉)
这一轮空袭的规模格外的大,除了“启明”、“太岁”和“鹰”号释放的舰载机,还有从莱城机场飞来的战机。
虽然延德岛机场的飞机也能为国防军提供支援,但这种多机场起飞战机在之前造成了一些意外,舰队错把澳军飞机当作延德岛机场飞来的己方飞机,让海湾里的战舰吃了几枚鱼雷。
不过,好在澳军使用的是美军的航空鱼雷,1943年时,美军曾对自家的MK13型鱼雷做过测试,结果在105次投弹中,只有不到20枚成功命中并爆炸,而在剩下的鱼雷中,各种故障都有。
虽然这一次失误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还是让国防军否定了多机场的作战方式,减少调度困难,改由莱城机场专门提供支援。
机群从澳军第9步兵师防线上空飞掠而过,澳军阵地瞬间被炸成了一片火海,500公斤的重磅炸弹落在地上,整个大地都象是被掀了起来一样,铺天盖地的烟尘笼罩了这片区域,数不清的碎木屑和碎土块稀里哗啦的掉落下来。
澳军士兵们蹲在堑壕的掩蔽部中,紧紧地抱着怀中的恩菲尔德步枪,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家就会被埋在掩蔽部底下。
在空军的狂轰滥炸之后,是野战炮群的炮击,城区的战斗已经结束,陆战三旅的炮兵也加入了战斗,相比于只有一个105mm榴弹炮炮兵营的第16师,陆战三旅的炮兵就要强出一头,再加上临时配属的1
(buduxs)?()50mm榴弹炮营,
火力的密度还是十分可观的。
在约2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后,
炮火就开始向后延伸,进攻也就正式打响。
在面前这个不比月球表面好多少的阵地上,军官吹响哨子,士官扯着嗓子大声催促,领着步兵准备进攻。
炮兵的效果固然可观,但效果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好,这篇阵地上的抵抗力量永远不会少了。
当炮火的巨响逐渐远离,坦克引擎的轰鸣主宰战场,澳军的军士官们便跌跌撞撞地在堑壕中奔跑、挥手来传递信息,收拢士兵,组织抵抗。
猛烈的炮击和空袭破坏了阵地上的障碍物,炸毁了交通壕,切断了野战电话,使得前后方失联,这是相当恐怖的。
只可惜,不待对方有所反应,几十辆坦克便出现在了战场上,无法计数的国防军步兵跟在坦克后方几米,小跑步地前进。
大的战术方面,国防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以钳形攻势紧逼澳军阵地,除了主攻方向,其他战线上也有一些兵力,营造出一副声势浩大的样子,让敌人分不清主攻方向,而刚刚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抵达莫尔兹比港的科科达支队也秘密参与了行动,在敌人的身后发动进攻。
而具体到战术上,国防军采取以中型坦克为矛头,重型坦克为中坚,步兵伴随的协同攻势,效果拔群。
当距离迫近到二三百米时,澳军的反坦克炮开始发力,澳军手中的反坦克炮虽然穿透力尚可,能够威胁到37式中型坦克,但炮弹的问题在面对37式坦克时反而更好,因为更厚的装甲所造成的炮弹碎片会加大这个铁坨子的杀伤力,这是能直接被穿的33式轻坦体验不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防军也开动脑筋,搞了许多办法,包括但不限于临时增加裙甲、堆放沙袋等。
当逼近到澳军一线阵地不足百米时,坦克们就会用火炮与机枪交替开火,尝试锁定并摧毁敌方的反坦克炮,而步兵们则会从坦克后面冲出来,向澳军阵地发动冲击。
然而,令吴培泉没想到的是9月7日的强攻依然被澳军挡了下来,澳军指挥官阿瑟·艾伦成功识破了国防军的进攻,南北两处攻势均被澳军瓦解。
反倒是科科达支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他们成功突破澳军阵地,搅得对方后方大乱,然而,他们也没想到澳大利亚人这么坚定和果决,连炮兵都拿着步枪战斗,竟然挡住了科科达支队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