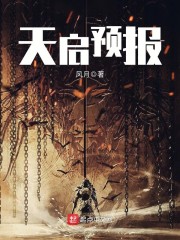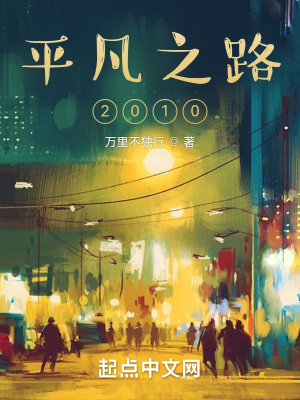52小说网>我的世界无尽幸运大陆 > 第1850章 苏州(第1页)
第1850章 苏州(第1页)
苏州府南郊,接官亭。
三日后,帝后銮驾如期抵达苏州府境。与扬州城外那肃杀压抑、草木皆兵的氛围截然不同,苏州府的迎驾之地,透着一股井然有序的从容。
官道两旁,依旧有府兵衙役值守维持秩序,但神情并不紧绷,也未将百姓远远驱离。许多百姓自发地聚集在稍远些的地方,带着好奇与敬畏的目光,安静地望向那支威严浩荡的队伍。田间劳作的农夫直起身子观望,河上撑船的船家也放缓了速度,一切都显得自然而平和。
接官亭前,以苏州知府周砚为首的一众官员,早已按品级肃立等候。周砚身着洗得发白却熨烫得一丝不苟的青色官袍,头戴乌纱,面容沉静,腰背挺直如松。他身后的僚属们虽也恭敬,却不见扬州官员那种如丧考妣的惊惶,更多的是一种等待检阅的沉稳。
当那象征着无上皇权的明黄九旒銮驾与深沉如墨的玄色王轿在御前铁骑的拱卫下缓缓停稳时,周砚率先上前一步,撩起官袍前襟,动作流畅而端正地跪拜下去,声音不高不低,沉稳清晰地响彻寂静的官道:
“臣,苏州知府周砚,率苏州府文武僚属,恭迎圣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迎并肩王千岁!千千岁!”
他身后的官员们也随之整齐跪拜,山呼声整齐划一,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腔调,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恭敬:
“恭迎圣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迎并肩王千岁!千千岁!”
銮驾的珠帘被内侍轻轻掀起。女帝秦玲身着杏黄常服,在徐姑姑的搀扶下步下銮驾。她凤眸扫过眼前跪拜的官员,目光在为首那位清癯沉稳的知府身上停留了一瞬。与扬州杨文显那谄媚惊惶的姿态不同,这位周知府,跪得端正,拜得沉稳,身上透着一股历经风霜后的从容与书卷气。
几乎同时,玄色王轿的门无声开启。并肩王孔衫玄袍玉带,身姿挺拔如渊渟岳峙,缓步而出。他那双深邃的眼眸,如同最精准的尺,瞬间便将眼前的一切景象纳入眼底——官员的仪态、士兵的神情、远处百姓的反应,以及为首那位知府身上洗得发白的官袍和沉稳的气度。
秦玲唇角微扬,露出一抹雍容平和的浅笑,声音清越,清晰地传入周砚等人耳中:“周卿家与众卿平身,不必多礼。”
“谢陛下隆恩!谢王爷隆恩!”周砚再次叩首,才领着众官从容起身。他垂手侍立,目光恭敬地落在帝后御阶之前的地面上,既不刻意谄媚仰望,也无丝毫躲闪怯懦。
孔衫的目光在周砚身上略作停留,并未言语。但周砚却敏锐地感觉到一股极其短暂、却仿佛能洞穿肺腑的审视感掠过自己,那感觉并不像扬州时那般带着冰冷的煞气,更像是一种…评估?他心中微凛,面上却依旧沉静如水。
秦玲的目光扫过周围井然有序的景象,以及远处那些并未被驱赶、只是安静观望的百姓,凤眸中的满意之色又深了一分。她温声道:“一路行来,观苏州之境,官道平整,阡陌井然,百姓神色安泰,颇有治世之象。周卿家治理有方,辛苦。”
周砚躬身,声音依旧平稳,无半分居功自傲:“陛下谬赞。此乃臣之本分,赖陛下洪福,苏州士民勤勉,方有今日景象。臣不敢言功,唯恐有负圣恩。”
孔衫此时也缓缓开口,低沉的声音带着一种惯常的平静,却让所有官员都不自觉地更加挺直了腰背:“治理一方,守土安民,本就是牧守之责。能守好这份本分,便已是难得。”
这话听在周砚耳中,更像是某种肯定,也像是一种无形的鞭策。他再次躬身:“王爷教诲,臣谨记于心。”
秦玲微微颔首,不再多言:“起驾吧。周卿家引路,入城。”
“臣遵旨。”周砚领命,侧身让开道路,动作干净利落。他并未像杨文显那般抢着引路表现,只是示意属下官员各归其位,自己则退至銮驾侧后方合适的位置,准备随驾而行。
仪仗再次启动。在周砚沉稳的引导下,庞大的队伍缓缓驶向苏州城门。沿途所见,商铺照常营业,行人往来有序,见到皇家仪仗虽敬畏避让,却无惊慌失措之态。偶尔有小儿啼哭,也很快被父母安抚。整座城池透出一种富庶安定下特有的从容与活力。
銮驾之内,秦玲与孔衫透过轻纱望向窗外。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致映入眼帘,空气中似乎都飘荡着水乡特有的温润气息。
“官清民顺,气象果然不同。”秦玲轻声道,语气带着一丝真正的轻松与欣赏。
孔衫的目光掠过井然有序的街道和那些面容平和的百姓,最终落在车窗外那道青色沉稳的背影上,深邃的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欣赏,低低应了一声:“嗯。此城此人,当得起‘清明’二字。”
车轮碾过苏州城古老的青石板路,发出平稳的辘辘声。这座以园林锦绣、文华鼎盛闻名天下的城池,以其特有的从容与秩序,迎接着来自帝国最高权力的审视。而那位身着半旧青袍的知府,正以他独有的方式,无声地向帝后诠释着何为真正的“官清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