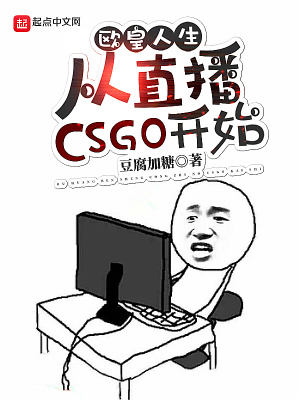52小说网>华娱从神棍到大娱乐家txt > 第五百八十六章 逃离大英博物馆为雪糕大佬加更(第7页)
第五百八十六章 逃离大英博物馆为雪糕大佬加更(第7页)
路宽站在她身侧,声音平静:“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幅临摹得次一些的,我关注过这种技法。”
“这叫‘高古游丝描’,”他手指虚点,引导着她的视线,“笔法连绵不断,匀细悠长,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衣袂的飘逸和人物的动感。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强调眼神是人物灵魂的窗口。你细看这些仕女的眼神,内敛而充满故事感,这是真正的‘以形写神’。”
“艺术都是相通的,这就好比演员的表演,其实也是自己在作画,形神如何表达?此处可见一斑。”
他顿了顿继续道:“这幅画的意义远不止艺术技巧的巅峰。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绢本人物画之一,是卷轴画形式的奠基之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儒家对女性的道德规训,用极具美感和叙事性的画面呈现出来,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的中国人物画创作。”
“只可惜。”路老板摇头,语调略有痛惜:“这样的国之瑰宝在这里并未得到应有的珍视。早年博物馆为了便于西方模式的展览,竟然听信日苯画家的建议将其裁切成三段,裱在木板上。”
“这种粗暴的处理方式对绢本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虽然后期尽力修复,但裂痕和掉粉的痕迹依然可见,这不仅是物理上的破坏,更是对画作气韵和完整叙事性的割裂。”
“就像一部完美的电影被外行瞎剪八剪,配乐配音镜头构图全部黯然失色,不复风采。”
突然一个略带不满的声音用流利的英语插了进来,带着一种学术上的优越感:
“对不起先生,你和这位女士从进门开始的言论,恕我直言,颇有偏颇之处。”
两人回头,正是刚才在门口欲言又止的亚裔年轻人,只不过两人适才都没注意到他。
后者胸前挂着显眼的工作牌,声音带着一丝刻意营造的权威感,仿佛在进行一场公开的讲解。
周围的游客,包括一些激动地认出了路宽和刘伊妃的中国留学生,都好奇地围拢过来,想听听这位博物馆工作人员要说什么。
“我是朱利安·庄(JulianZhuang)。”他朗声自我介绍,目光扫过渐渐聚拢的人群,带着几分骄矜。
“我的家族经营艺术品收藏与投资,我本人业于牛津大学东方研究系,是现任馆长的学生,也兼职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中国书画的助理策展人。”
他倒觉得没有必要上来就介绍自己的家世,而是特意强调了自己的学术背景,显然很享受这种在众人面前“以正视听”的感觉。
只不过目光再次扫过路宽和刘伊妃时,似乎从周围一些华人游客兴奋的低语和举起的手机中察觉到了什么,语气略带惊讶地挑挑眉:“看样子……二位似乎是知名人士?”
路宽淡然一笑,也不管他是真认不得、还是假认不得:“算不上,不过我很好奇你既然听得懂中文,为什么偏要用英语与我们交谈?你是哪里人?”
朱利安·庄微微一怔,长着青春痘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混合着优越感和疏离的神情,继续用英语回答:“我听得懂中文,但我不大会讲,我是香江人,拥有英国国籍。”
几乎难以遮掩的,这位牛津高材生的慕洋自豪和满足感已经像狐臭一样溢出了。
“这与我们讨论的话题无关,”他迅速将话题拉回,语气重新变得强硬,“也许你在你的领域很有名,但我必须纠正你关于这幅画以及本馆收藏理念的错误认知!”
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显然,这场辩论的火药味开始浓了起来。
朱利安·庄开始了他的论述,内容与之前类似,强调博物馆的“保护功绩”和“全人类共享”的理念。
只不过在路老板听来,更显得像是为殖民历史辩护的陈词滥调。
“你这番普世价值的高论听起来冠冕堂皇,却巧妙地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关于权力与掠夺的历史原罪。”
“请你诚实地告诉在场的每一位游客。”路宽的手指向《女史箴图》,“这幅画,以及这间展厅里无数来自中国、希腊、埃及、非洲的珍宝,它们来到这里的首要原因,究竟是你所说的‘无私保护’,还是伴随着枪炮、条约和不平等交易的赤裸裸的掠夺?”
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让整个区域瞬间安静下来。
今天在场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甚至有不小比例的亚裔人群,此刻颇为感同身受。
“你熟练地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镀金。但我想请问,作为一名血管里流淌着华夏血液的华人,当你面对这些被迫远离故土、承载着母国文明记忆的瑰宝时,你内心深处,可曾有过一丝一毫对于它们真正归属的思考?可曾有过一丝一毫对于其来源国人民情感创伤的共情?”
这番话如同匕首,直接刺向朱利安·庄身份认同中最矛盾、最可能不堪一击的部分。
朱利安·庄的脸瞬间涨红,路宽的质问像一把尖刀,剥开了他精心维护的学术外衣,直刺内心最不愿面对的身份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