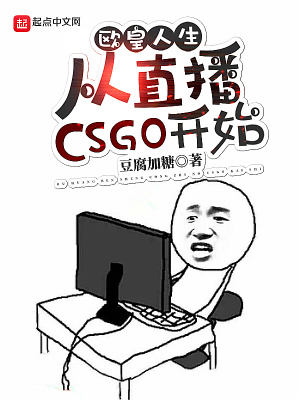52小说网>罗汉伏魔从倚天屠龙开始92yanqing > 第95章 暗流汹涌(第3页)
第95章 暗流汹涌(第3页)
向问天脸上浮现一丝尴尬,心中暗暗叹道:“这圣姑也太聪明了!”
任我行轻轻咳了两声,故作镇定地换了个话题:“女儿,我这十几年来,好多问题都思索明白了,可只有一件事,没想明白,你自幼聪慧,替我想想。”
任盈盈道:“什么?”
任我行道:“我在黑牢中静心思索,对东方不败的种种奸谋已一一想得明白,只是他何以迫不及待地忽然发难,至今仍想他不通。
本来嘛,东方不败对向兄弟颇有所忌,怕我说不定会将教主之位传了给他。但向兄弟既不别而行,我又将《葵花宝典》传了给他。
这宝典历来均是上代教主传给下一代教主,原是向他表明清楚:不久之后,我便会以教主之位相授。
唉,东方不败是个聪明人,这教主之位明明已交在他手里,他为什么这样心急,不肯等到我正式召开总坛,正式公布于众?却偏偏要干这叛逆篡位之事?”
他皱起了眉头,似乎直到此刻,对这件事仍弄不明白。
任盈盈秀眉微蹙。
向问天道:“他一来是等不及,不知教主到何时才正式相传;二来是不放心,只怕突然之间,大事有变。”
任我行道:“其实他一切已部署妥当,又怕什么突然之间大事有变?”
任盈盈道:“该不会是因为那年我在端午节大宴说的话吧?”
“端午节?”任我行又是不解。搔了搔头,道:“你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说过什么话啊?那有什么干系?”
任盈盈瞥了父亲一眼,低声道:“爹爹,是女儿不好。”
向问天笑道:“教主别说小姐是小孩子。她聪明伶俐,心思之巧,实不输于大人。那一年小姐是七岁吧?她在席上点点人数,忽然问你:‘爹爹,怎么咱们每年端午节喝酒,一年总是少一个人?’你一怔,问道,‘什么一年少一个人?’”
任盈盈道:“我说,我记得去年有十一个人,前年有十二个。今年一、二、三、四、五……咱们只剩下了十个,你当时就拉下了脸。”
任我行心想:“这倒显得我这个做父亲的有些愚钝啊!”良久,他才转头看向女儿,忍不住问道:“女儿,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任盈盈唇角微勾:“那时候我就是看人少了,我没想别的。”看着父亲:“爹,你就别问这些了,现在当务之急得铲除东方不败,一旦等他得知消息,必然会提高警惕,也会对我们下毒手。”
任我行定了定神,说道:“你想让我同意云长空所请?”
任盈盈小声说道:“虽说东方不败一直欺瞒于众,说爹爹已经逝世,可你一旦重出江湖,恐怕会有不少人觉得他对爹爹没有下杀手,待我也很好,恐怕还会说他待人仁义呢!我们人微力弱,难改大局,正好仰仗云公子的武功。”
任我行轻轻点了点头:“这世道本来就是黑白颠倒,黑白不分,将恩将仇报以下犯上,说成仁义之事,古往今来,比比皆是。
只是盈盈,你可想过,云长空为何要帮我们?他既然对你无意,何必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趟这浑水?”
任盈盈道:“你不信他想一会天下第一高手的想法?”
任我行冷哼一声:“西湖牢底十二年不见天日,我不相信任何人!”
任盈盈道:“也包括我与向叔叔了?”
“咳、咳咳咳……”向问天差点被呛到。
任我行更是连忙摆手道:“为父不是那个意思!为父的意思是……你觉得,云长空像个弱冠之年的年轻人吗?”
他话声一落,向问天连忙抢前一步,朝任盈盈抱拳一拱,道:“大小姐,云长空说话不亢不卑,气派极大,根本不像是个弱冠之人,倒像是个久走江湖,且取得极大名位的中年人,他一心要上黑木崖,此事不可不防!”
任盈盈闻言之下,先是一怔,继而心头一紧,她也意识到了。
任我行道:“所以他说是要随着我们与东方不败一会,可如果不是呢?我等几人一上黑木崖,必然引起大乱。
倘若他乘着我神教内乱,再与那些所谓名门正派中人里应外合,我日月神教的基业或许都会毁在他的身上,爹爹有何面目去见祖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