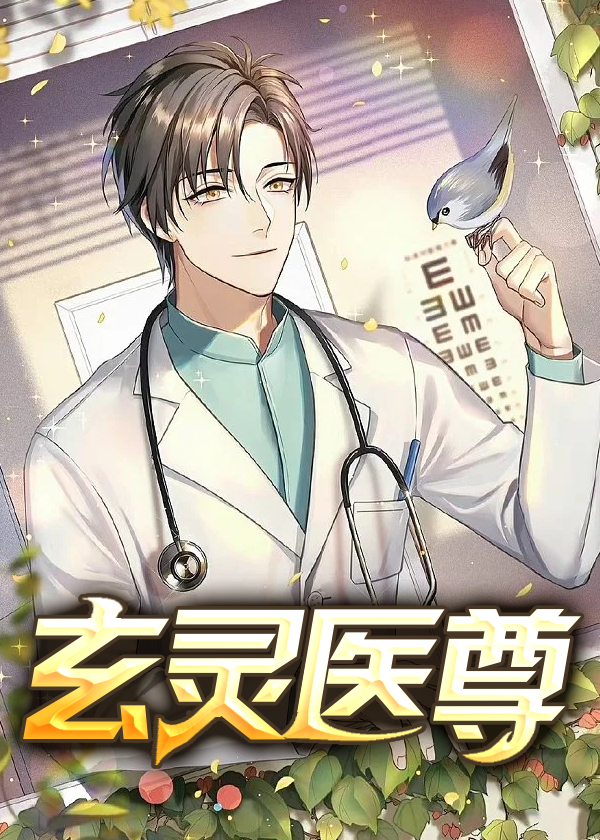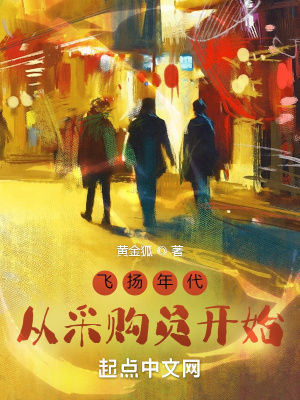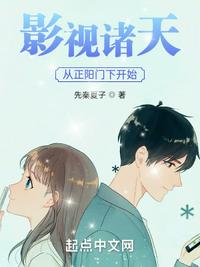52小说网>从负债百万到最强锦衣卫TXT > 第937章 给脸不要脸那就不给脸(第1页)
第937章 给脸不要脸那就不给脸(第1页)
赢高治闻言,沉吟良久。
他原本觉得这催一催的法子,多少有点无聊,甚至带着点莫名其妙的小家子气。
但听李北玄这么一解释,却忽然意识到。
这手段说不上高明,却极其实在,极其有效。
没错。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崔仲琛到底说不说得出个所以然,也不在于他背后藏了多少人、牵了多少线、动了多少心思。
哪怕真有证据,真有罪证,到了那一步,再谈惩处、谈退让、谈收场都不迟。
但眼下最不能放任的,是这个架势。
崔仲琛不能就这么风风光光、气定神闲地走进晋阳。
不能以那种我是来评理的姿态,来面对朝廷。
他是一个臣。
而现在出了事,是晋地出了乱子,是朝廷要查,是皇室要追责。
崔仲琛若真心想澄清、想解释、想撇清自己,那就该低头赴讯、收敛锋芒、主动配合。
可他偏不。
他现在这一路走得,不紧不慢,不疾不徐,从清河出发到如今,整整走了半月有余。
地方州府无不设宴相迎,沿路门生故吏相随而行,就连地方文士也纷纷写诗送行,赞其“此行如夜照寒星、清光直捣晋阳”。
一切动作,都在告诉天下人,他不是来谢罪的,是来镇场子的,是来理清是非、主持大义的。
他把自己当成了裁判。
那赢高治算什么?
朝廷算什么?
难不成要真把他迎进府衙、备茶设案、请上主位,听他问一句:“晋阳之乱,究竟几人主谋?”
那还谈什么震慑?还谈什么定分止争?
这不是来问罪的,是来分权的。
是来教朝廷如何收场,如何宽仁,如何维护士族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