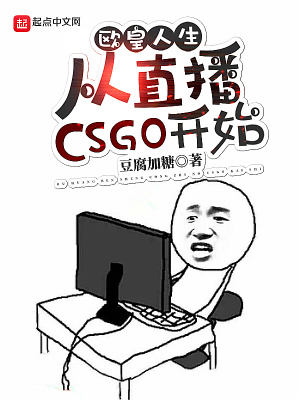52小说网>寿衣店好干吗 > 第442章 智能手环一二九(第1页)
第442章 智能手环一二九(第1页)
他面容俊美却毫无生气,浓密的黑色长发如同海藻般铺散在洁白的枕头上,衬得那张脸更加苍白如纸,仿佛沉睡千年的古尸。
床边,坐着一个同样年轻的男子——炽烈。他背脊挺得笔直,像一尊沉默的雕塑,年轻的脸庞上却顶着一头刺眼的花白头发,形成一种诡异的不协调感。
他的眼睛,深邃得如同不见底的寒潭,此刻正一瞬不瞬地、死死地盯着床上沉睡的人,那专注的姿态仿佛要将对方的灵魂从沉睡中硬生生拽出来。
病房门被无声地推开,一股浓烈到呛人的香水味瞬间打破了死寂。一个穿着昂贵皮草、珠光宝气、脸上妆容厚得如同面具的妇人,扭着腰肢走了进来。她脸上堆着过分热情的笑容,目标明确地走向炽烈。
“哎哟,长使大人啊,”妇人声音又尖又嗲,带着刻意讨好的腔调,不由分说地就伸出戴满戒指、指甲油鲜红刺目的双手,紧紧握住了炽烈放在床边的手,“咱们教主这……到底要昏睡多久啊?可真是急死个人了!”她的手指,带着一种粘腻的触感,在炽烈的手背上若有似无地摩挲着。
炽烈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他虽不通太多人情世故,对凡人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也常感迷惑,但此刻,一种极其怪异的、带着强烈占有欲和亵渎意味的“念”,如同实质的、带着腥甜气息的黯黑色气体,正从这个老女人身上弥漫出来,无声无息地缠绕上他的手臂,甚至试图钻进他的皮肤。
那不是杀意,却比杀意更让他感到一种源自本能的、冰冷的厌恶。
“咳咳……”炽烈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轻咳,既是生理上的不适,也是某种力量的引动。他那双非人的竖瞳深处,金芒一闪而逝。目光如同最精密的扫描仪,瞬间穿透妇人华丽的皮囊和厚厚的粉底,直接“看”到了她体内气息的流转。
某个代表着淫邪与欲念的窍穴,正如同溃烂的伤口,源源不断地向外泄露着浑浊的、令人作呕的阳气或者说,生命元精的劣化形态。
炽烈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厌烦。他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懒得用任何法术技巧,意念如同最精准的手术刀,又像一块冰冷的烙铁,顺着那股污秽气息的来路,直接、粗暴地“堵”了上去!
“呃!”妇人浑身猛地一僵,像被无形的电流击中。紧接着,她眼中那层浑浊的、充满欲望的迷蒙雾气瞬间褪去,眼神变得异常清明,甚至带着一丝茫然和……空洞。仿佛刚才那些龌龊的心思从未存在过,整个人都被强行“格式化”了。
“教主具体醒来的时间,无人能定。”炽烈冰冷的声音响起,毫无波澜,仿佛刚才只是拂去一粒灰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的目光扫过妇人略显呆滞的脸,“你最近一段时日,恐怕不会再起那些无谓的、污秽的念头了。”
妇人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身体的本能反应和炽烈话语中那毫不掩饰的冰冷与警告,让她瞬间如坠冰窟,一股巨大的羞耻感猛地涌上心头。
她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慌乱地松开手,像被什么东西烫到一样,语无伦次地丢下一句:“啊……我、我去喝个咖啡……长使大人您忙!”话音未落,人已经像受惊的兔子般,仓惶地扭身,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出了病房,厚重的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声关上,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迅速远去,消失。
炽烈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重新定格在病床上沉睡的教主脸上,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空气中残留的浓烈香水味,证明着刚才那场短暂而令人作呕的插曲。
色心既起,秽气自生。
在炽烈这条真龙的眼中,凡人的龌龊心思,不过是清晰可见的、散发着恶臭的污浊之气罢了。被当面戳穿,又岂有颜面再留?
林兰正好看到了这个老太婆飞奔出去的画面,似乎此时躺在床上的炽烈也有了一丝感应,面部表情变作微笑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