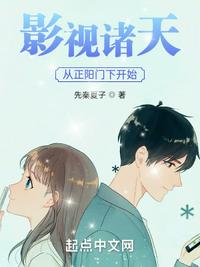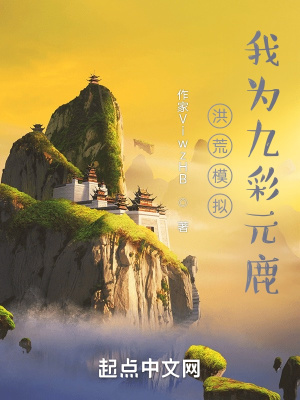52小说网>地府创造 > 第142章(第1页)
第142章(第1页)
第142章
关于“是否有用”的话题,穆祺并未作出明确回复,或者说他本人实在也不知道,这苦心积虑的一套操作到底能不能行。
当然,在一开始做决策的时候,穆祺就曾深思熟虑的考量过,伴随着炼铁技术被一起撒播出去的还有挖煤选矿的技术,期盼着这些从关中扩散到地方的小官能够建立一个最基础、最原始、勉强可以自行循环的工业体系:用挖到的煤炼铁,再用炼出来的铁挖出更多的煤,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展现工业化自动增殖的效力;而附带着送出去的造纸技术和农具锻造,则是为了消化多余的钢铁,扩展新的市场需求。
总的来说,设想非常美好。也许在起步阶段这些散播出去的种子还需要启动资金、生产工具,以及权力的一点小小倾斜;但只要站稳脚跟存活下来,这一套体系应该就应该能够自动增殖、自动扩张,不必依靠皇权的荫蔽,也可以很好的延续下去。
不过,理论归理论,设想归设想,但到底能有几成胜算,穆祺自己心里也在打鼓。说白了,工业化扩张不是两眼一瞪双手一摊,念个咒语就能成功的美差;脱离了完整成熟的供应链以及全国市场之后,这玩意儿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玄学……要在一片蛮荒的浑茫地带筚路蓝缕,开启山林,难度之大,真有匪夷所思之感——在这样的难度下,十成中能有个一成可以存活,那都算是侥幸之至了。
可是,现在是在甲方面前做汇报,面对着给人给钱支持不遗余力的甲方,你还厚着脸皮说项目难度很大麻烦很多投钱不一定有回报成功率不到一成,那多半是好日子过久了皮发痒了急需铁拳松一松皮;为了表示对甲方的尊重,穆祺踌躇片刻,只能道:
“这原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不必再说什么了。皇帝陛下是何等人物?只要听到什么“不是一朝一夕”、“从长计议”之类的套话,那真是抬一抬屁股都能猜出对方真正的意思。所以他只哼了一声,冷声开口:
“不是一朝一夕,那到底要有多久,才能见效?”
“也许,也许要有个一年多吧……”
“也许”要有个一年多吗?坦率来讲,穆祺并不知道这个“也许”的准确与否——说实话,这种纯粹白纸作画的工业起步谁也没有经验,更不说精确估计个一年多了;实际上,他费力憋出这么个数字来,纯粹是觉得刘登的耐心估计只有那么一两年,要是——要是一两年之间还不出了结果,那甲方的态度,恐怕就……
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能不能令甲方满意,不过他的脸色并没有变化。
“说得好。”
皇帝淡淡道:“既然这样,朕就一年以后派人下去看看,检查检查成效,如何?”
一日后,天子再下圣旨,决定全面推行巡视制度,由关中挑选官吏任为“直指使者”,每年奔赴各处,检视各地长吏的施政,进贤黜不肖,以做警示云云。
不过,皇帝的急躁还是大大超出了正常人的估计,虽然口口声声要“一年以后再看”,但实际上只过了七八个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召见了一批从江南调到关中任职的循吏,表面上是让这些人御前述职,实际上还是以某种旁敲侧击的姿态,在暗戳戳地试探,试探他先前撒播出去的人才,是否已经发生效用。
从结果来看,试探的结论确实相当令人满意。所以召见完官吏后,皇帝又马不停蹄的见了那个死鬼——(居然愿意和死鬼见面,可见真的是非常高兴);而在秘密会谈两刻钟后,老登同样如沐春风的逛了回来,甚至还顺手给手下带来了几件礼物——两把钢刀,一本油纸书,各自赏赐下去。
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显然就是上林苑的学员下乡之后,在当地生产出来的工业品——钢刀代表重工业,油纸代表轻工业;虽然质量上并不能与实验室中精心设计的样品相比,但也还算相当过得去;如果与先前粗制滥造、近乎于原始产物的玩意儿相较,那就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堪称开天辟地的产物。不能不令老登大为欣喜,乃至微微生出得意。
按照他先前的分配,这两把刀是送给长平侯与冠军侯的礼物,油纸书则是塞给穆某人涨涨见识,看一看他们大汉官吏在发展工业上的积极主动,高超水平——至少不比现代人差些什么。可是,礼物摆到桌子上以后,穆某人居然毫不客气,一把就抓住了钢刀,一把抽出,上下左右的打量。
诶不是,你看得懂你就上手?你连水果刀都没怎么摸过吧?
果然,上下左右打量一阵之后,穆某人又将钢刀合入刀鞘,双手捧给长平侯:
“卫将军以为,这把刀如何呢?”
卫将军还能以为如何?难道君主辛辛苦苦带回来的礼物(好吧也未必有多么辛苦),他还能说一句“不好”么?他只能回答:
“很不错。”
确实也算不错,虽然没有详细试刀,但看一看材质也算上佳,“不错”两个字,还是担得的。
“仅仅是不错吗?”
穆祺不动声色:“卫将军不觉得,这个形制很熟悉吗?”
他刷一声又抽出了钢刀,只见刀身细长,刀口熠熠闪光,刀刃与常见的军中形制迥然不同,倒更像是他们先前随手就能摸出来一把的……水果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