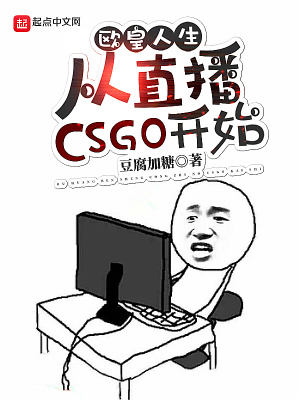52小说网>救赎相对应的情侣名 > 16第十六章(第1页)
16第十六章(第1页)
这出荒诞的闹剧,在老虎轰然倒下后,终于结束了。
因为院子里赶来了几个众宾客,包括五皇子都始料未及的人。
靖国公并着脸色发黑的建德帝,出现在了院门口。
段行川擦了把汗,也不知道该说老爷子来得及时,还是不及时。
因为老虎倒下而热沸的气氛倏地被泼了瓢冷水,不少人仿佛这才后知后觉,被关在笼子里的,姑且也是个皇子。
满院人呼啦跪了一地,齐呼万岁。
注意到建德帝的脸色,五皇子头皮一麻,跟着跪了下来:“……父皇。”
二皇子跪着也不嫌累,笑眯眯开口:“啊呀,父皇来晚了一步,错过了五弟的好戏。”
五皇子消停了半个月,建德帝忙政务忙得头疼,突然听闻五皇子趁着生辰宴,在全京城世家贵族面前又搞了出事,简直要气吐血。
再被二皇子这么一煽风点火,一时也顾不得皇家体面,怒斥:“你五弟胡闹,作为兄长,你不干涉管教,反倒纵容,在这里说风凉话!”
二皇子无所谓地低头认错,幽幽叹气:“儿臣知错,只是……儿臣哪儿敢管五弟呢。”
满院子的人不敢抬头,只剩靖国公和盛迟忌还站着。
靖国公看看地上的兽尸,又看了看盛迟忌,眼底闪过丝惊异。
建德帝望向被关在笼中的盛迟忌、倒在地上的尸体以及那一泊凝固的血,脸色却很难好看起来,从牙缝里磨出一声:“盛泊庭!”
五皇子活了快十八岁,头一次被皇帝爹连名带姓叫,心尖霎时抖了抖,止不住发慌。
他上次被禁闭半月,连累母妃,自觉丢尽脸面,这次生辰宴,母家的表兄送来只拔了牙的病虎,给他出主意,当着宾客的面整治一番盛迟忌。
他脑子虽然空空,但隐约察觉到盛迟忌似乎很在意谢元提——也正常,几个皇子谁不盯着谢元提,便以谢元提生病,他若是想出宫探望,他可以帮忙,哄骗盛迟忌来生辰宴,没想到盛迟忌居然答应了。
一只病虎而已,盛迟忌应该也死不了,至于其他后果,他并不考虑。
这会儿表兄满头大汗地跪在旁边,五皇子不敢吱声,拼命示意身边的内侍去开锁。
身旁的小内侍哆哆嗦嗦地掏出钥匙,走到铁门边时,差点绊一跤,手抖了几下,才把钥匙插。进去,打开了铁笼门。
沉重的嘎吱一声响起,浓重的血腥味仿佛扑鼻而来。
建德帝仿佛又衰老了几岁,深深地吐出口气,勉强在一堆宾客面前压住了脾气:“大夫呢?还不速速将七殿下扶下去治伤!”
跟在后头的侍卫听令上前,走到铁笼边,又迟疑着止住了步子。
冬日的衣裳颇厚,但盛迟忌身上的衣裳却明显被血洇湿,一片一片的浸着深色,高束的乌发也散乱了下来,半遮着的脸上都是血,染得低垂的眉目愈显冰冷深戾。
他手背上青筋微突,死死握在掌心的匕首还在滴滴答答淌着血,在脚下汇聚出血泊,看得人心头发寒。
像只浴血胜利的凶兽,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遍体鳞伤,却没人敢接近。
那一身锐气叫人忌惮,但他被关在铁笼中,收敛了危险感,让建德帝难得地感到了几分愧疚。
这个小儿子在外流浪多年,他本该疼爱补偿,但那身宁折不弯的骨头和野性不驯的性子,却叫他极为不喜。
况且随着风言风语愈演愈烈,他也不禁开始狐疑,盛迟忌的容貌和性子完全不似他,莫非真不是他的血脉……可他的眉眼,与记忆中的女人,又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