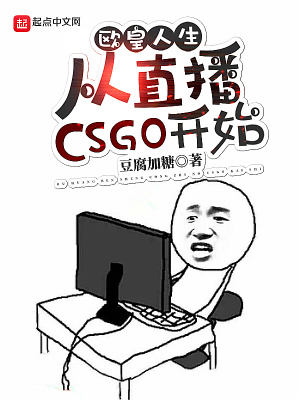52小说网>龙头铡 > 第808章 意外收获(第1页)
第808章 意外收获(第1页)
我们的车子返回工地时,已经是午夜的十二点多了。
本来可以更快点的,可天津范这货就跟特么丢了魂似得,一会儿说手机落医院,一会儿又嚷嚷着要买几副感冒药,磨磨唧唧来回折腾了能有四五轮。
此时,大部分工棚都已经黑了灯,只有最东头那片空地上还亮着刺眼的光,齐恒正带着他手底下的那帮“文化人”围着篝火瞎晃,有人弹着吉他跑调跑到天边,有人举着啤酒瓶嚎叫,闹得好像在开联欢会似的。
“操他妈的!损篮子!”
我低声骂了句,心里的火“噌”地就上来了。
老子忙得火烧眉毛,这帮狗贼倒有闲心载歌载舞,真把工地当度假村了?
“我特么过去一脚给狗日的啤酒全踢飞!”
老毕往窗外啐了口,骂骂咧咧地说要过去掀摊子,被我一把按住了。
“别叽霸添乱了。”
我咬着牙摆摆手压火:“抓紧歇着去吧,明天还有一大堆破事儿呢。”
我的小破房在工棚最里头,推开门时愣了一下,床上的旧床单被换成了干净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连墙角堆着的脏衣服都被挪到了一边。
扫了眼四周,没见到其他人,估计是哪个兄弟顺手给收拾的,也没多想,脱了外套就躺了下去。
摸出手机给安澜发了条信息,告诉她这边一切安好。
她回得很快,问我是不是又熬夜了,让我早点休息。
有一搭没一搭聊了几句,眼皮越来越沉,没多久我就睡着了。
再次睁眼,天已经透亮了。
窗外传来打桩机“哐哐”的巨响,震得土墙都在颤。
我揉着太阳穴坐起来,刚推开门就闻到了股油条和豆浆的香味。
简易小桌旁围了一圈人,二盼正叼着油条扒拉手机,老毕呼噜噜喝着豆浆,天津范和初夏凑在一起嘀咕着什么,旁边还蹲着两个熟悉的身影,牛奋和赵勇超,这俩眼下带着黑圈,显然是熬了一夜。
“醒了?”
二盼抬头朝我招手:“林夕买的早饭,赶紧来吃。”
我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的小伙,正是昨晚在医院碰到的那个林夕,他手里还拎着个空塑料袋,见我看他,腼腆地笑了笑:“大哥,不知道你爱吃啥,就多买了点。”
“谢了昂,来坐下一块对付口呗。”
我拿起根油条坐下,林夕忽然凑近一步,笑着打趣:“大哥,昨晚上睡得舒服吗?”
我愣了一下,好奇地上下扫量他。
“昨晚从医院出来以后,我又回了趟工地,看你屋头有点乱,就顺手帮你把被褥收拾了一下,卫生也打扫了打扫,其他人的我也没落下,就是夏夏姐没敢收拾的太认真,怕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