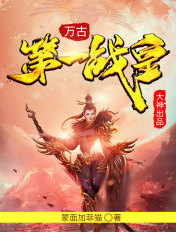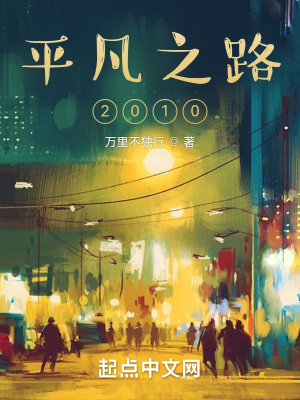52小说网>女扮男装我拿到登基剧本(科举)笔趣阁 > 5060(第55页)
5060(第55页)
例如孟丞,他习的一手好筝,刚进来没多久便被精通音律的侍书大人要过去一起编修古乐书去了。
而顾文淮稍稍吃亏了一些,音律、绘画等才艺是需要大量银钱去培养的,在这方面他便显得局促了不少。
而贺云昭相比之下倒是受到重用,因有曲瞻的引荐,她一早便得了陛下的赏识,常往太极殿为陛下整理奏折。
贺云昭抓住了机会,她小心观察着皇帝的习惯,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当然,最重要的是把握朝堂上的局势,这从各地呈递上来的奏折上都能看出一二。
她不仅仅是整理,还会根据轻重缓急将最要紧的事放在最上面。
同时若是一件事有两种看法,那她会将这二位官员呈递的奏折放在一处,这样陛下在看的时候,便能在同一个时间看到两个方向的看法,不会因为时间差导致先入为主。
有这样一位修撰在身侧,李燧处理起朝政来可以说是效率倍增。
且从前那些编修、庶吉士整理奏折时只是看,他们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记住了东西记的也是各位阁老的批语。
但贺云昭不同,她几乎是在脑子里做好了一个思维导图,并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一个事件为中心。
只要陛下问,她立刻能将看过的奏折里的情况如实复述出来、不论是刑事案件、运河用料还是银钱使用,她开口就能报个七七八八。
有一日梁阁老到太极殿与陛下商议金水河防涝之事,道是今秋需征调民夫前去修缮河堤。
李燧蹙眉道:“朕仿佛记得去年已经修过一次了?”
他眼睛一瞟看到贺云昭在一侧整理奏折,便问道:“是不是有人呈上过。”
贺云昭稍一回忆便脱口而出,道:“四月初冀州刺史上书称金水河两侧堤坝牢固,两岸百姓早早准备引水种地。”
“另有丰庆十二年户部拨了两万两银子修缮,工部认为不够,又拨了五千两。”
梁阁老听的简直呆住了,李燧也愣住了,两人同时瞧着贺云昭。
既是曾经连续修了两次,还花费了大价钱,四月冀州刺史又禀堤坝稳固,那为何又有工部上书提拔需要修缮。
若是这段时间内涨水了为何不见当地官员上书禀告?
此事必有内情,李燧便摆手叫梁阁老停下,吩咐人前去调查此事。
贺云昭能做到如此地步那自然不是因为她天生就有什么过目不忘的本领。
是因她在整理奏折时会刻意仔细看这些固定好的数字、时间、地点,人名不必记得太清,记得姓氏就是。
贺云昭有官瘾,要是在翰林院每日修书治学,她不见得多有精神,虽也专注但不够积极。
但在太极殿接触第一手的朝政信息就不同了,她劲头足的很!
她恨不得一整天待在太极殿做事,而皇帝又是个脾气好爱夸赞人的,惹得贺云昭一天天充满了力气!
同样的道理,每日写稿子写的人都没了精神,但要是跟在最大的领导身边指点江山,那是每时每刻都新鲜刺激。
她表现的实在出众,于是每次到太极殿,皇帝都安排她整理奏折。
有她这样的卷王在太极殿,皇帝处理朝政的效率都变高了。
但唯独有一个问题,皇帝也需要休息啊!
李燧甚至感觉贺云昭在太极殿这些日子是他皇帝生涯中最勤政的一段时间。
每当他看到贺云昭一手翻看着奏折一手将要点写在宣纸上,他总有一种被追着努力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