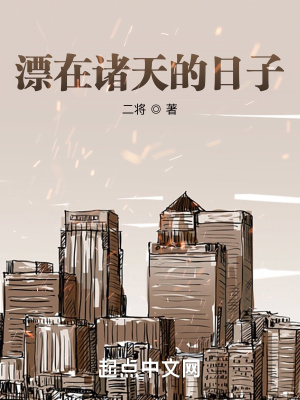52小说网>明末奋斗有个客机空间 > 第250章 开垦荒地 锄头比刀剑更能稳天下(第1页)
第250章 开垦荒地 锄头比刀剑更能稳天下(第1页)
新兵训练结束的第二天,林缚就给他们派了个新任务——扛锄头。
不是去打仗,也不是去巡逻,是去军屯东边的荒坡开垦荒地。三十多个新兵背着锄头站在坡下,个个脸都绿了。王二柱举着那把刻着“智”字的短刀,跟举着块烙铁似的:“大人,咱们是兵,不是农夫!拿锄头算啥?”
林缚正在看荒地的地形图,闻言头也没抬:“兵能饿着肚子打仗?这荒坡要是种上麦子,明年能多收五十石,够你们吃三个月。是锄头管用,还是你手里的刀管用?”
王二柱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想起小时候,家里要是没粮,爹就得拿着锄头去山里开荒,哪怕挖出块石头地,也得种上几棵土豆。那时候,锄头确实比啥都管用。
赵虎凑过来,小声说:“大人,让当兵的种地,会不会让人笑话?京营的兵,连马都不用自己喂。”
“笑话?”林缚笑了,指着坡上的石头,“去年冬天,有三个流民冻饿而死,就躺在那棵老槐树下。你说,是让他们笑话,还是让流民饿死?”
赵虎不说话了。他知道,林缚说的是实话。军屯的粮食虽然够吃,但周边的流民越来越多,不多开点荒地,明年春天肯定要出乱子。
开荒这活,比训练还累。荒坡上全是石头,一锄头下去,“当”的一声,震得手发麻,地里只留下个白印。王二柱急了,掏出短刀就想挖,被林缚拦住了。
“用这个,”林缚递给他一把铁镐,“石头得用镐刨,就像打仗遇着盾,得用锤砸。光用刀,有啥用?”
王二柱接过铁镐,吭哧吭哧刨起来。没刨几下,手心就磨出了血泡,疼得他龇牙咧嘴。旁边的新兵们也好不到哪去,有的锄头像举不动,有的一使劲把锄柄弄断了,活像群没头的苍蝇。
陈老兵背着筐路过,见了这景象,放下筐蹲下来,拿起锄头示范:“刨石头得找缝,就像给牲口卸套,得顺着劲。你看——”他把锄头尖插进石缝,轻轻一撬,一块碗大的石头就滚了下来。
“还是陈叔厉害!”新兵们围过去,眼睛都亮了。
陈老兵笑了:“我种了一辈子地,就这点本事。你们别小看这锄头,它能种出粮食,能喂饱人,比啥都金贵。”
这话没错。到了中午,新兵们饿得前胸贴后背,看着坡下农户送来的窝头,个个跟狼似的抢着吃。王二柱啃着窝头,突然说:“原来这窝头,是用锄头种出来的。”
林缚坐在坡上,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对赵虎说:“你看,他们现在觉得锄头沉,等明年麦子长出来,就知道这锄头有多轻了。刀剑能守住粮仓,却长不出粮食。天下要稳,先得让百姓有饭吃,这就得靠锄头。”
赵虎点点头,拿起锄头也刨起来。他刨得不快,但很稳,一下一下,像在敲鼓。新兵们见统领都动手了,也跟着卖力干起来,荒坡上响起一片“叮叮当当”的镐声,倒像支特别的军乐。
开荒的消息传到镇上,有人笑话:“林大人的兵,是种地的兵。”这话传到林缚耳朵里,他不光没生气,还让人把这话写在布告栏上,旁边加了句:“能种地的兵,才是好兵。”
没过几天,怪事发生了。周边的流民听说军屯在开荒,居然有二十多个主动跑来帮忙,不要工钱,只要管饭。为首的是个瞎了只眼的老汉,姓刘,据说以前是种庄稼的好手,因为战乱瞎了眼,才成了流民。
“林大人,”刘老汉摸着地里的土,“这土是好土,就是石头多。要是能把石头捡出去,再施点肥,种麦子保准行。”
林缚眼睛一亮:“刘大爷,您要是肯留下指导,我给您记工分,年底能换粮食。”
刘老汉赶紧摆手:“不用不用,管饭就行。只要能让这地长出粮食,我就知足。”
有了老农户指导,开荒的进度快多了。刘老汉虽然瞎了眼,但凭着手感,能摸出哪块土能种,哪块得扔石头。王二柱跟着他学,居然也练出了本事,一锄头下去,能准确避开石头根。
“二柱啊,”刘老汉摸着他的手,“你这手,是握刀的手,也是握锄头的手。握刀能杀人,握锄头能活人。活人,总比杀人强。”
王二柱心里一动,想起训练时沙盘上的“战场”,突然觉得,这荒坡其实也是个战场,对手是石头和贫瘠,武器是锄头和汗水,赢了,就能长出粮食,就能活人。
东林党听说林缚让士兵种地,又开始在朝堂上吵。有个御史写了篇奏折,说“林缚本末倒置,令士兵弃武从文(农),动摇国本”,还说“如此下去,军不成军,国将不国”。
崇祯看着奏折,又批了三个字:朕知道了。但他让人给军屯送了批新锄头,还附了句话:“好好种,朕等着吃新麦。”
赵虎拿着皇帝的亲笔信,在新兵面前炫耀:“看见没?皇上都支持咱们种地!”
王二柱挠挠头:“皇上是不是也觉得,锄头比刀管用?”
“傻小子,”赵虎拍他一下,“皇上是觉得,有粮食,才能有天下。”
开荒开到一半,遇上了麻烦。荒坡下有块地,归镇上的劣绅李剥皮所有。李剥皮自己不种,也不让别人种,说是“自家祖坟的风水地”。新兵们挖到地界时,李剥皮带着家丁赶来,举着鞭子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