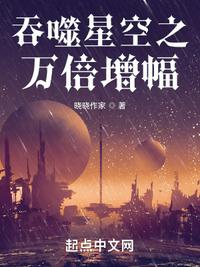52小说网>明末奋斗有个客机空间 > 第248章 皇帝的朱批 朕知道了其实啥也不知道(第1页)
第248章 皇帝的朱批 朕知道了其实啥也不知道(第1页)
崇祯皇帝把弹劾奏折扔进垃圾桶的第三天,在一份军屯送粮的奏报上,写下了三个字:朕知道了。
这三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墨色饱满,看着颇有帝王气概。可要是凑近了看,能发现“道”字的最后一捺,微微有些颤抖——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前一晚没睡好,被东林党和阉党余孽的争吵闹得头疼。
“皇上,”大太监王承恩捧着杯参茶,小心翼翼地说,“这军屯的粮,比去年多了三成,真是可喜可贺。”
崇祯放下朱笔,揉了揉太阳穴:“可喜可贺?你没看周御史的奏折?说林缚用妖法催熟粮食,那些麦子看着饱满,其实是空壳,吃了会拉肚子。”
王承恩嘴角抽了抽:“皇上,周御史前几天还说林缚是当代董卓,这会又说他用妖法,他自己怕是都忘了前半句。”
“朕也忘了,”崇祯拿起军屯的奏报,上面附着张粮田照片——是林缚让人用西洋相机拍的,金灿灿的麦田一望无际。皇帝盯着照片看了半天,突然问:“这西洋玩意儿,真能把麦子照下来?不会是林缚画的吧?”
王承恩苦笑:“皇上,相机这东西,奴才见过,确实能把东西照下来,跟镜子似的,一点不差。”
崇祯没说话,又拿起一份奏折,是户部尚书写的,说军屯的新式水车如何厉害,请求在全国推广。皇帝看了两行,又拿起周御史的反驳奏折,说“水车转动会惊动龙脉,导致天灾”。
“龙脉?”崇祯烦躁地把奏折扔在桌上,“去年黄河决堤,龙脉咋没显灵?今年军屯用水车,倒惊动龙脉了?这些文官的嘴,真是比棉裤腰还松,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王承恩不敢接话,只是默默地给皇帝续茶。他伺候崇祯这么多年,知道这位皇上的难处——朝堂上吵成一锅粥,边关告急的文书堆成山,国库比脸还干净,现在连个军屯的水车,都能吵出“龙脉”来。
没过几天,崇祯又收到份密报,是刘守有送来的,说周御史不仅收了张敬的银子,还偷偷在城外买了处宅子,养了个戏子,天天在家唱《长生殿》。
“长生殿?”崇祯气得拍了桌子,“国难当头,他还有心思看戏?传旨,把周御史的官帽摘了,让他回老家种地去!”
王承恩刚要应声,崇祯又摆摆手:“算了,摘了他的帽,东林党又要吵。让刘守有把这事压下去,别再让他上奏折就行。”
皇帝心里清楚,现在的朝堂,就像个漏风的破船,只能慢慢补,不能猛劲凿。周御史是东林党的骨干,真把他撸了,朝堂上能吵翻天,到时候别说推广水车,怕是连军粮都运不出去。
这种“明知不对,却只能忍着”的滋味,崇祯尝了不少。就像上次张敬案,明明知道还有不少人涉案,却只能抓几个典型,剩下的,只能让他们“戴罪立功”——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军屯的奏报越来越多,有说新式农具好用的,有说百姓生活改善的,还有请求派农技人员指导的。崇祯每份都看,看完都批三个字:朕知道了。
赵虎拿着抄来的朱批,笑得直不起腰:“大人,皇上这是啥意思?知道了,然后呢?是支持还是反对啊?”
林缚正在调试新造的播种机,闻言头也没抬:“这就够了。皇上说‘知道了’,就是告诉那些想找茬的文官,他盯着军屯呢,别太过分。至于支持还是反对,现在不重要。”
“为啥不重要?”赵虎不解。
“因为军屯的麦子,不会因为皇上说‘支持’就多收一石,也不会因为说‘反对’就少收一粒。”林缚放下扳手,“咱们把自己的事做好,粮食打多了,百姓吃饱了,皇上自然会支持。现在吵再多,都没用。”
这话传到京城,王承恩把意思转给了崇祯。皇帝听完,沉默了半天,突然说:“林缚这小子,比朝堂上的那些文官明白多了。”
明白归明白,该批的“朕知道了”,还得继续批。有次军屯报上来,说培育出一种新稻种,能在盐碱地生长。崇祯批完三个字,突然对王承恩说:“你说,这稻种真能在盐碱地长?”
王承恩想了想:“皇上,要不……让人去军屯取点稻种,在京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