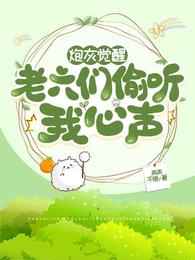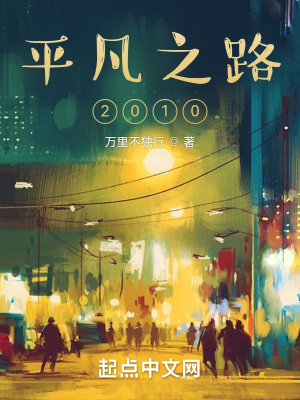52小说网>关我什么事儿类似 > 第1402章 像爷爷的李枋(第2页)
第1402章 像爷爷的李枋(第2页)
“就是,乔阿姨,您先带他们进去,我来弄。”李乐把李笙塞给曾老师,就去了车后。
“走吧,乔婶。”
“那。。。诶,好。”
至于一家人为什么没去市里,原因其实是张稚秀年纪大了,耐不得市区的热。
这两年,自打进夏天,便习惯去朱家角这里,保姆乔阿娣家里避暑。
之前说过,乔阿娣外婆就是张家的“娘姨”,之后又是她妈,再到她,直到解放后,张家老太爷去世,才遣散了家里的这些老人。
一直到八十年代,乔阿娣才又重新回到张雉秀身边,从三十多岁干到现在,自己也成了外婆。
这种绵延三四代的关系,早已经让乔阿娣成了半个张家人,外婆妈妈都是张家给养老。
而这处在朱家角的宅子,就是张稚秀出钱,把乔阿娣家的老房子在原有的底子上,改造扩建成的一处三进四院。
“张师傅,一起吃个饭。”
“不了不了,我这得赶紧去这边的分公司交接一下,晚上好赶上回临安的火车。”
“好嘛,敢情你们这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儿啊?”
“呵呵,是啊,杜组长说了,别的我们管不着,大小姐用车上面,我们不能耽误事儿。”
“那行,就不留你了。”李乐点点头,背包里扯出一条利群阳光来,拍到司机手里,“您拿着路上抽。”
“不是,李先生,这个。。。。。”司机往回推,但哪推得过。
“行了,拿着吧,这几天辛苦您了。”
“谢谢李先生。”
“客气啥,以后回临安,少不得麻烦您。”
“那我帮你把箱子搬进去。”
“放门厅就成。剩下我来。”
送走司机,李乐把门一关,转身进了小院儿。
过门楼是一道窄窄甬道,碎石子铺地,两侧植着南天竹,绿叶子里缀满红珠儿。拐角处摆着几盆矮松,虬枝盘结在紫砂盆里,根爪抠着太湖石,倒像活了百年的老精怪。
粉墙斑驳处爬满忍冬藤,细碎的白花藏在绿叶里,像旧宣纸上洇开的淡墨。
前院天井里铺着青苔石板,四角檐头滴落的雨水在凹槽里汇成细流,沿着铜钱纹的石砌暗沟往南淌,四水归堂的格局带着南方民居的精细。
井台边青砖沁着水汽,苔痕从砖缝里漫出来,直爬到井沿刻着"丙寅年造"的字迹旁。
转过云纹砖雕的月洞门,中庭里立着三叠太湖石,石缝间斜插着半人高的罗汉松盆景。青砖围起的花坛里,文竹细叶筛碎日影,腊梅枝子倒比花时更见筋骨。
穿过按照旧时规制摆放着家具的中厅,就见到一座二层小楼,木楼梯藏在西厢房后头。
花窗正对着葫芦形鱼池,不过丈许,池底铺着雨花石,几尾红鲤在睡莲叶底逡巡,搅得浮萍时聚时散,倒像谁打翻了青釉瓷盘里的丹青。
东南角葡萄架漏下满地碎金,紫藤虽过了花期,虬曲的老根倒把木格窗衬得愈发清俊。两边甬道铺着"人"字青砖,砖缝里钻出几簇狗尾草,风过时,轻轻挠白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