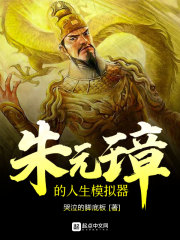52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57章 燕居之境 圣人的日常(第1页)
第157章 燕居之境 圣人的日常(第1页)
燕居的本质,是“与自己相处的能力”。《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自省不是自我批判,而是与自己对话,在对话中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会犯错,像孔子“过则勿惮改”;接纳自己有欲望,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却“不多食”;明白自己有局限,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自我接纳,让燕居时“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就像接纳了不完美的玉石,才能雕琢出温润的光泽。现代心理学中的“自我关怀”,与这种能力高度契合——对自己友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觉察自己的情绪,这些都是燕居时内外合一的基础。
从孔子的燕居到当代人的生活,“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的状态始终是修身的目标。它告诉我们:忙碌时的担当与闲居时的从容,本是一体两面——没有朝堂上的“克己复礼”,便没有燕居时的“申申如也”;没有对“仁”的追求,便没有“夭夭如也”的神情。外在的礼仪与内在的修养,当能和谐统一——就像优美的乐曲,既要有音符的规律(礼),也要有情感的流动(仁)。正如《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笃志是“公堂”的担当,切问近思是“燕居”的修养,二者结合,便是完整的君子人格。
暮色中的阙里,孔子放下手中的《诗经》,起身走到庭院。杏花落在他的肩头,他抬手拂去,动作舒展而温和,像春风拂过花瓣。弟子们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明白:“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不是模仿可得的姿态,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后的自然绽放。这种燕居之境,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在忙碌后能舒展身体,在喧嚣中能温润神情,便是在靠近孔子的“申申”与“夭夭”,便是在践行“素其位而行”的古老智慧。